凌晨三点,市医院输液大厅依旧灯火通明,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疲惫的味道。
咳嗽声、孩子的哭闹声、低声交谈混杂在一起,嗡嗡地响。
我独自缩在冰凉的塑料椅上,右手手背埋着针,透明的药液一滴一滴缓慢地往下掉,像永远也流不完。
脑袋昏沉得像灌了铅,每一次眼皮不受控制地耷拉下去,又都会猛地惊醒,强撑着抬眼去确认那还剩大半瓶的吊瓶。
不敢睡。
周围都是陌生人,有的有家属陪着,低声说着话,有的靠在一旁打盹,只有我,只有我是一个人。
生病时的孤独和脆弱被无限放大,鼻子发酸,只能用力吸一下,把那股委屈憋回去。
就在这时,对面一道灼灼的视线让我下意识抬头。
隔着一排座椅,对面坐了个染着奶奶灰发色的帅哥,穿着潮牌,正瞪大了眼睛看着我,表情活像见了鬼。
我的老天奶!
这不是陆哥手机屏保上的那个女人?!
一道清晰又夸张的声音猛地砸进我几乎停转的脑子。
我愣住了,茫然地眨了眨眼。
幻听?
烧糊涂了?
我下意识像吃瓜群众一样,偷偷四下乱瞄,想找出他“心声”里说的那个“屏保上的女人”。
这大厅里人满为患,说不定是哪个角落藏着故事。
大半夜孤零零一个人输液,陆哥知道不得心疼死?
那道声音又响起来了,语气里带着一种发现惊天大秘密的兴奋和幸灾乐祸。
我僵住了,血液好像凝滞了一瞬。
这声音……好像不是通过耳朵听见的?
它直接出现在我脑海里?
而对面那个帅哥,的的确确没有开口说话!
他只是盯着我,手指在手机屏幕上无意识地摩挲。
我现在给陆哥打电话,他不得飞奔过来?
心跳骤然失序。
陆哥?
哪个陆哥?
我认识的人里,只有他……姓陆。
不,不可能。
绝对不可能。
三年前分手时话说得那么决绝,他那样骄傲一个人,怎么还会留着我的照片当屏保?
又怎么可能为我心疼?
一定是生病出现幻听了。
我努力说服自己,试图忽略心底那丝不该冒头的、微弱的悸动。
却见对面那帅哥眼神飘忽了一下,忽然做贼似的举起手机,摄像头不偏不倚,正对着我的方向。
“咔嚓——”极其轻微的快门声,在一片嘈杂里几乎微不可闻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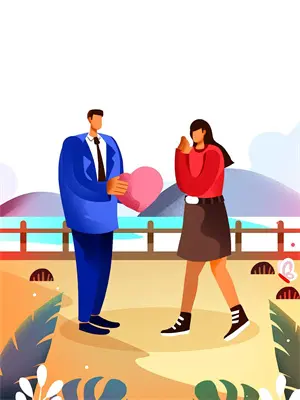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